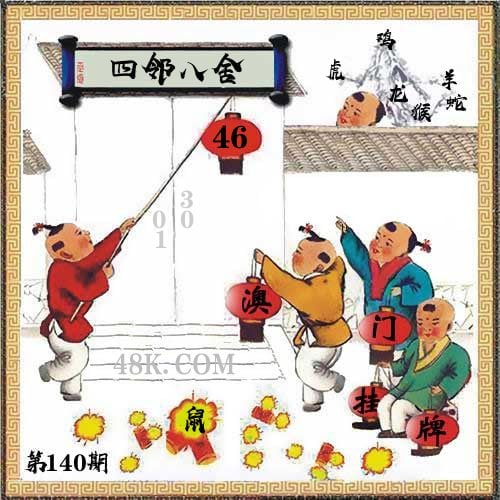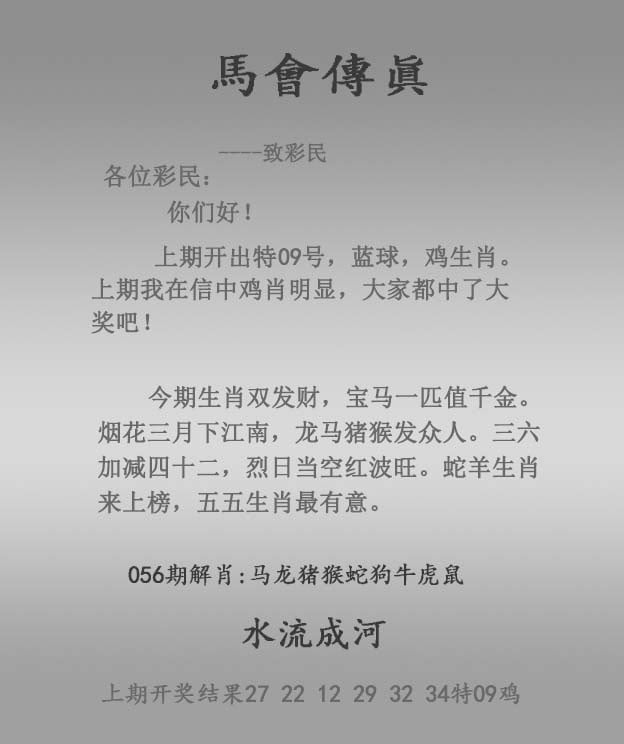- 140期:【贴身侍从】必中双波 已公开
- 140期:【过路友人】一码中特 已公开
- 140期:【熬出头儿】绝杀两肖 已公开
- 140期:【匆匆一见】稳杀5码 已公开
- 140期:【风尘满身】绝杀①尾 已公开
- 140期:【秋冬冗长】禁二合数 已公开
- 140期:【三分酒意】绝杀一头 已公开
- 140期:【最爱自己】必出24码 已公开
- 140期:【猫三狗四】绝杀一段 已公开
- 140期:【白衫学长】绝杀一肖 已公开
- 140期:【满目河山】双波中 已公开
- 140期:【寥若星辰】特码3行 已公开
- 140期:【凡间来客】七尾中特 已公开
- 140期:【川岛出逃】双波中特 已公开
- 140期:【初心依旧】绝杀四肖 已公开
- 140期:【真知灼见】7肖中特 已公开
- 140期:【四虎归山】特码单双 已公开
- 140期:【夜晚归客】八肖选 已公开
- 140期:【夏日奇遇】稳杀二尾 已公开
- 140期:【感慨人生】平特一肖 已公开
- 140期:【回忆往事】男女中特 已公开
- 140期:【疯狂一夜】单双中特 已公开
- 140期:【道士出山】绝杀二肖 已公开
- 140期:【相逢一笑】六肖中特 已公开
- 140期:【两只老虎】绝杀半波 已公开
- 140期:【无地自容】绝杀三肖 已公开
- 140期:【凉亭相遇】六肖中 已公开
- 140期:【我本闲凉】稳杀12码 已公开
- 140期:【兴趣部落】必中波色 已公开
| 140期:澳门天天好彩AA级公开; 还等啥大胆砸 |
|---|
| 140期:精选九肖:虎鸡牛蛇狗鼠龙马猴 |
| 140期:精选六肖:虎鸡牛蛇狗鼠 |
| 140期:精选四肖:虎鸡牛蛇 |
| 140期:精选三肖:虎鸡牛 |
| 140期:精选二肖:虎鸡 |
| 140期:精选一肖:虎 |
| 140期:精选尾数:5.7.1.0.9 |
| 140期:家禽野兽:野兽 |
| 140期:平特一肖:双数 |
| 140期:精选十码:16.28.09.29.25.08.18.38.36.34 |
| 140期:精选五码:16.28.09.29.25 |
| 140期:精选三码:16.28.09 |
| 六合活动进行中:站长担保 点击投注 |
| 140期:精选一码:重拳出击-16-信心十足 |
| 138期:澳门天天好彩AA级公开; 还等啥大胆砸 |
|---|
| 138期:精选九肖:虎牛鼠鸡蛇龙猪羊兔 |
| 138期:精选六肖:虎牛鼠鸡蛇龙 |
| 138期:精选四肖:虎牛鼠鸡 |
| 138期:精选三肖:虎牛鼠 |
| 138期:精选二肖:虎牛 |
| 138期:精选尾数:1.9.4.2.7 |
| 六合活动进行中:站长担保 点击投注 |
| 137期:澳门天天好彩AA级公开; 还等啥大胆砸 |
|---|
| 137期:精选九肖:蛇龙狗猴虎兔猪牛马 |
| 137期:精选十码:25.37.14.08.34.16.15.19.29.36 |
| 六合活动进行中:站长担保 点击投注 |
- 澳门四不像精解
- 香港四不像精解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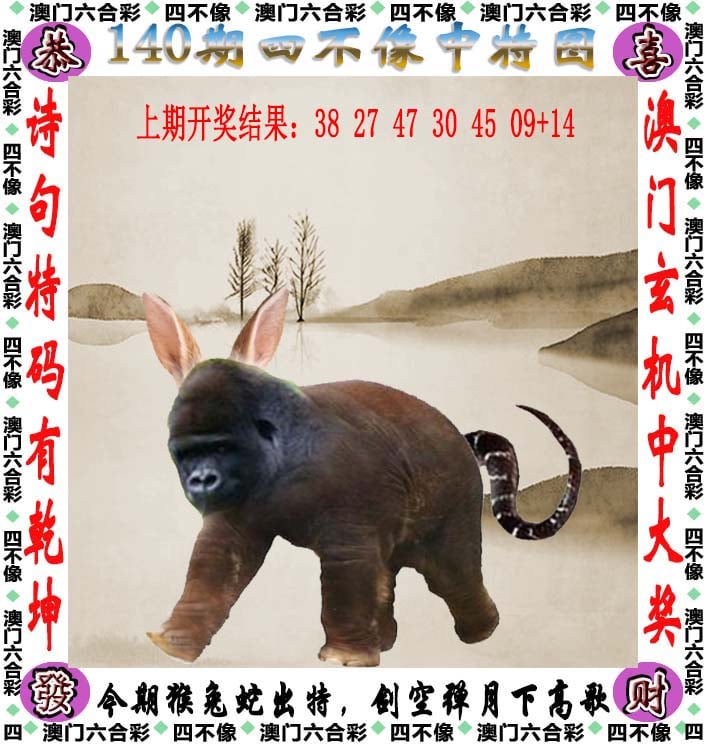
140期今期猴免蛇出特,剑空弹月下高歌开?00准
①杀鸡羊牛(09.21.33.45.11.23.35.47.05.17.29.41)
②图解特肖猴免蛇马猪
③合双+大数
更多资料尽在650288.com
138期今期马鼠鸡出特,独倚高楼望眼宽开牛41准
①杀羊龙狗(11.23.35.47.02.14.26.38.08.20.32.44)
②图解特肖马鼠鸡猴牛
③合单+大数
更多资料尽在650288.com
- 澳门平特心水
- 香港平特心水
140期平猪→猪蛇(2连)→猪蛇龙(3连)
139期平兔→兔马(2连)→兔马牛(3连)
- 澳门传真
- 香港传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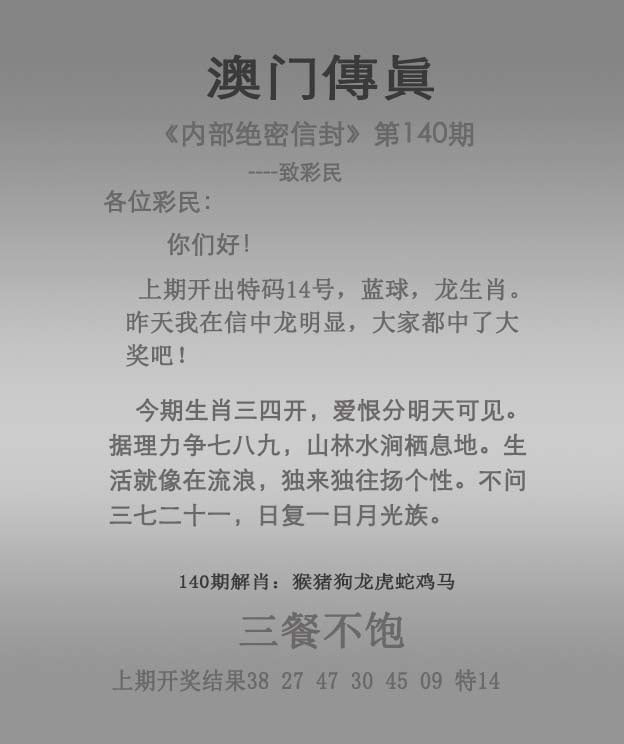
澳门传真140期
解:“三四开”如兔(机敏)试探,龙(变幻)藏玄机;“爱恨分明”是马(烈性)与鸡(果断),锋芒毕现;“七八九争”似猴(灵巧)斗鼠(狡黠),虎(威势)镇场;“山林水涧”属蛇(隐忍)栖猪(随遇),漂泊如流浪。生肖暗喻世相:兔疑、龙变、马躁、鸡锐、猴争、蛇蛰、猪淡,道尽月光族随性而活的浮世绘
七肖:兔龙马鸡猴蛇猪
五肖:兔龙马鸡猴
三肖:兔龙马
主特:15.27.14.26.24.36.09.34.25.19
更多资料尽在650288.com
澳门传真139期
解:三六开暗指生肖虎(寅为三,六合马,虎马争雄);不弃不馁如生肖牛(勤耕不辍,终得丰收);零八一七谐音鸡(0形蛋,8似双翅,17为酉鸡排位);星火燎原喻生肖龙(火旺腾云,势不可挡);一天八杯指生肖猪(亥水主饮,福态安康);九宫八卦隐生肖蛇(巳火居巽位,盘绕如卦象);春泥护花比生肖兔(卯木生春,润物无声)。(注:7生肖含虎、牛、鸡、龙、猪、蛇、兔)
七肖:虎牛鸡龙猪蛇兔
五肖:虎牛鸡龙猪
三肖:虎牛鸡
主特:28.40.17.29.09.21.14.31.25.27
更多资料尽在650288.com
澳门传真138期
解:本期生肖运势波折(二七开指机遇与风险并存),前行之路多阻碍;特定数字(一二四七)可能带来财运,但借贷易、偿还难;金钱困局能压垮豪杰,若不用钱财谋事,反遭讥讽太清高;利益面前,真情假意立现。【生肖演绎】牛倔强闯关,却困于借贷泥潭;虎威风陷二七险局,跋涉艰难;兔灵巧押一二四七,得失无常;蛇算计反被债缠身;马奔劳为财,英雄气短;猴机敏却笑他人太清廉;狗忠义难抵金钱试炼。七生肖皆陷财局,道尽世态炎凉。(选牛、虎、兔、蛇、马、猴、狗,以拼搏、机变、忠厚等特质呼应诗句中的金钱困境与人情冷暖。)
七肖:牛虎兔蛇马猴狗
五肖:牛虎兔蛇马
三肖:牛虎兔
主特:17.29.16.28.15.27.37.38.34.08
更多资料尽在650288.com
澳门传真137期
解:三一开似虎啸山林,王者气魄震千古;口口相传如龙吟九霄,威名远播永流芳。二七陌路若蛇与兔,同林却难共途(地支巳卯不相合);血染苍天见马奔沙场,赤胆忠魂冲云霄。勇往直前似狗守信念,冷眼众议亦无悔。风雨共度如鸡鸣偕老,双影仗剑伴斜阳。(含虎、龙、蛇、兔、马、狗、鸡七生肖)注:诗句暗藏豪情壮志与江湖侠义,生肖化喻更显命运交错——兔蛇缘浅、龙虎争辉、犬马效忠,终成侠侣传奇
七肖:虎龙蛇兔马狗鸡
五肖:虎龙蛇兔马
三肖:虎龙蛇
主特:16.28.14.26.25.37.15.36.08.09
更多资料尽在650288.com
- 澳门五肖十码
- 香港五肖十码
140期推荐⑤肖:猪牛马鼠狗
140期推荐③肖:猪牛马
140期推荐⑩码:07.19.05.17.24.36.06.18.08.32
140期推荐⑤码:07.19.05.17.24
更多资料尽在650288.com
139期推荐⑤肖:龙羊狗鸡猪
139期推荐③肖:龙羊狗
139期推荐⑩码:14.26.23.35.08.20.09.21.19.31
139期推荐⑤码:14.26.23.35.08
更多资料尽在650288.com
- 澳门红字肖
- 香港红字肖
140期红字暗码【性烈如火】【02 19 23 40】
解析:性:性情,脾气。形容性情暴躁。出处 明 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第六三回。解蛇鼠鸡虎兔猴
解取特肖:蛇鼠鸡虎兔猴
解取五肖:蛇鼠鸡虎兔
解取四肖:蛇鼠鸡虎
138期红字暗码【画地为牢】【08 13 20 39】
解析:意思是在地上画一个圈当做监狱,比喻只准在指定范围内活动。解羊狗鼠猪牛蛇
解取特肖:羊狗鼠猪牛蛇
解取五肖:羊狗鼠猪牛
解取四肖:羊狗鼠猪
137期红字暗码【坐井观天】【05 18 35 47】
解析:意思是坐在井底看天,比喻视野狭窄、见识短浅,无法认识到更广阔的世界。解龙马蛇虎鼠猪
解取特肖:龙马蛇虎鼠猪
解取五肖:龙马蛇虎鼠
解取四肖:龙马蛇虎
- 澳门平五不中
- 香港平五不中
140期【40.46.11.12.07】?
138期【46.09.24.31.12】准
- 澳门传真20码
- 香港传真20码
140期澳门内幕传真20码开?00
特码玄机:472 156(虎16)12+16= ?
码海扬帆三八开,辞旧迎新四九来
提供20码:
24 45 28 06 46 17 18 01 22 42
12 04 05 26 16 47 44 19 39 43
138期澳门内幕传真20码开牛41
特码玄机:276 105(鼠18)27+12= ?
一条大路通南山,山里野兽靠天管
提供20码:
05 35 38 40 21 32 17 07 26 34
33 06 13 15 10 47 02 41 27 03
136期澳门内幕传真20码开鸡09
特码玄机:276 134(猴34)18+08= ?
地仙亦是三千岁,木落山空君未归
提供20码:
18 34 23 47 36 21 04 32 01 41
22 12 35 09 07 42 40 03 24 46
135期澳门内幕传真20码开蛇37
特码玄机:305 285(猪31)26+12= ?
日照山林闪绿光,暗香疏影蓝花香
提供20码:
07 05 22 08 28 26 33 37 41 10
42 19 15 48 29 18 27 46 35 21
- 澳门精准单双
- 香港精准单双
140期精准单双〖双数〗开:?00准
139期精准单双〖双数〗开:龙14准
138期精准单双〖单数〗开:牛41准
136期精准单双〖单数〗开:鸡09准
135期精准单双〖单数〗开:蛇37准
133期精准单双〖双数〗开:猴10准
132期精准单双〖双数〗开:龙02准
129期精准单双〖双数〗开:虎40准
126期精准单双〖双数〗开:龙02准
125期精准单双〖单数〗开:蛇49准
123期精准单双〖单数〗开:鸡45准
122期精准单双〖单数〗开:鸡33准
120期精准单双〖双数〗开:虎28准
119期精准单双〖双数〗开:龙38准
118期精准单双〖双数〗开:马36准
- 澳门玄机诗
- 香港玄机诗
140期【澳彩玄机诗】
台上戏一场,雪月惹人迷:开?00
解:
139期【澳彩玄机诗】
娇女十八变,戴玉伴人皇:开?00
解:特码开龙14
138期【澳彩玄机诗】
六畜吃西餐,警惕在旁观:开牛41
解:特码开牛41
137期【澳彩玄机诗】
水秀景万千,作主探心机:开马36
解:特码开马36
136期【澳彩玄机诗】
看人低一等,好龙假大空:开鸡09
解:特码开鸡09
- 澳门跑狗图
- 香港跑狗图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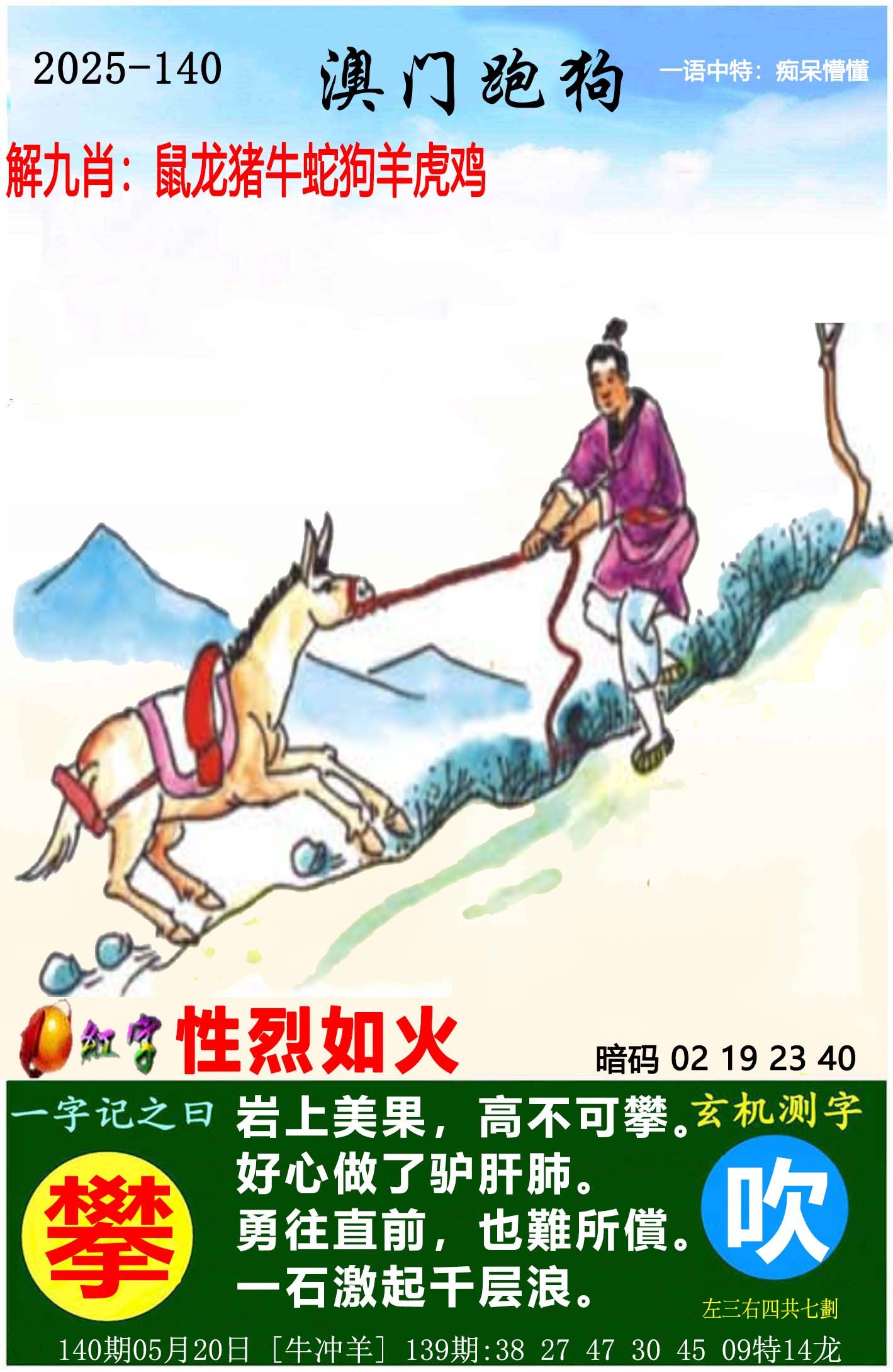
140期跑狗一字記之曰:【攀】
岩上美果,高不可攀。好心做了驴肝肺
勇往直前,也難所償。一石激起干层浪
解:岩上美果如猴(机灵)垂涎却难摘,虎(勇猛)强攻反落空;驴肝肺似马(赤诚)付出,反被蛇(多疑)误解;勇往直前若龙(刚烈)冲刺,终难如愿;一石千浪是鼠(敏锐)点破,引发波澜。生肖映人性:猴贪、虎莽、马冤、蛇冷、龙倔——道尽世事无常,好心未必得好报的无奈
五肖:猴虎马蛇龙
四肖:猴虎马蛇
三肖:猴虎马
二肖:猴虎
一肖:猴
137期跑狗一字記之曰:【蠢】
攀上巅峰,才知愚蠢;直随秋风冠边城
朝來寒雨,晚來狂風!三追六七有一连
解:攀上巅峰如虎踞山巅,方知孤高反成困;秋风冠城似马踏边关,意气风发终散尽。寒雨狂风中,鸡鸣破晓却湿羽,狗守城门啃冷骨。忽见三追六七谜底现——原是龙潜深渊笑众生,何必执着争高低?(虎、马、鸡、狗、龙五生肖,暗喻成败皆空)注:五兽映心境——虎马争胜时,鸡狗受苦日,真龙早看透。数字玄机藏三六九等,争到巅峰,不过秋风一笑
五肖:虎马鸡狗龙
四肖:虎马鸡狗
三肖:虎马鸡
二肖:虎马
一肖:虎
135期跑狗一字記之曰:【黄】
再坐一會,一等再等;从来好事多磨折
踪影查然,空餘遺恨!峭出家门知世情
解:这几句写人生等待与遗憾——再坐一会如蛇般徘徊,一等再等似牛般固执;好事多磨像虎遇坎坷,踪影杳然若龙逝无痕;初知世情是鼠的警觉。五生肖喻世态:蛇的犹豫、牛的忍耐、虎的波折、龙的幻灭、鼠的清醒,道尽人间事与愿违之常态
五肖:蛇牛虎龙鼠
四肖:蛇牛虎龙
三肖:蛇牛虎
二肖:蛇牛
一肖:蛇
134期跑狗一字記之曰:【息】
朦朦胧胧,翻手为云,云四合一现跟七
潮涨潮落,永垂干古,似醉未醉七分醉
解:【玄机点破】朦朦胧胧如兔(卯)隐雾中;翻手为云是龙(辰)布雨势;云四合一现马(午7)踏云来;潮涨潮落应猴(申)戏东海;七分醉留鸡(酉)立斜阳。生肖点睛:龙卷风云马嘶鸣,兔隐烟纱猴弄潮;独留金鸡摇醉步,半醒半梦演逍遥。(取龙、马、兔、猴、鸡,以飘渺之姿暗合天道无常)
五肖:龙马兔猴鸡
四肖:龙马兔猴
三肖:龙马兔
二肖:龙马
一肖:龙
132期跑狗一字記之曰:【控】
生死大權,由誰操控?時乖運蹇龍變蟲
仰人鼻息,忍辱負重。終有一日風雷動
解:生死大權:象征绝对权威,对应龙(真龙天子,掌控生死)龍變蟲:权贵失势,暗指蛇(小龙堕落为虫)仰人鼻息:卑微求生,关联狗(摇尾乞怜)忍辱負重:坚韧不屈,代表牛(忍辱耕耘)風雷動:逆袭爆发,呼应马(一鸣惊人)生肖表达龙(权柄在握)、蛇(贵贱无常)、狗(卑微求生)、牛(隐忍蓄力)、马(逆境突围)(注:精选5个最具戏剧张力的生肖,通过极盛-堕落-隐忍-爆发的命运曲线,展现权力更迭的残酷与希望。)
五肖:龙蛇狗牛马
四肖:龙蛇狗牛
三肖:龙蛇狗
二肖:龙蛇
一肖:龙
- 澳门绝杀三只
- 香港绝杀三只
140期绝杀三只【羊蛇龙】开?00准
139期绝杀三只【虎鸡蛇】开龙14准
138期绝杀三只【蛇马虎】开牛41准
137期绝杀三只【鼠狗蛇】开马36准
136期绝杀三只【羊蛇鼠】开鸡09准
134期绝杀三只【猪马猴】开龙14准
133期绝杀三只【鼠蛇兔】开猴10准
132期绝杀三只【鸡鼠猪】开龙02准
129期绝杀三只【马鸡狗】开虎40准
128期绝杀三只【羊马猴】开蛇13准
126期绝杀三只【羊虎狗】开龙02准
125期绝杀三只【虎马鸡】开蛇49准
124期绝杀三只【牛兔狗】开猴10准
- 澳门藏宝图
- 香港藏宝图

140期平特藏宝图玄机
【今期唯有旺三三】
解:今期唯有旺三三,平特虎兔
特码范围评估:02-29
推荐平码:18.09.08.17.19.20
开奖结果:00-00-00-00-00-00T00
139期平特藏宝图玄机
【今期道人送金火】
解:今期道人送金火,平特猴鸡
特码范围评估:01-17
推荐平码:19.09.07.17.29.20
开奖结果:38-27-47-30-45-09T14
136期平特藏宝图玄机
【今期生肖定龙蛇】
解:今期生肖定龙蛇,平特龙蛇
特码范围评估:02-18
推荐平码:11.02.03.18.20.19
开奖结果:31-23-25-33-02-21T09
134期平特藏宝图玄机
【红波旺势不可挡】
解:红波旺势不可挡,平特虎狗
特码范围评估:02-10
推荐平码:12.01.03.17.21.18
开奖结果:38-27-04-23-06-34T14
133期平特藏宝图玄机
【今期生肖六六来】
解:今期生肖六六来,平特蛇鼠
特码范围评估:01-09
推荐平码:10.02.03.18.20.09
开奖结果:45-03-16-01-21-38T10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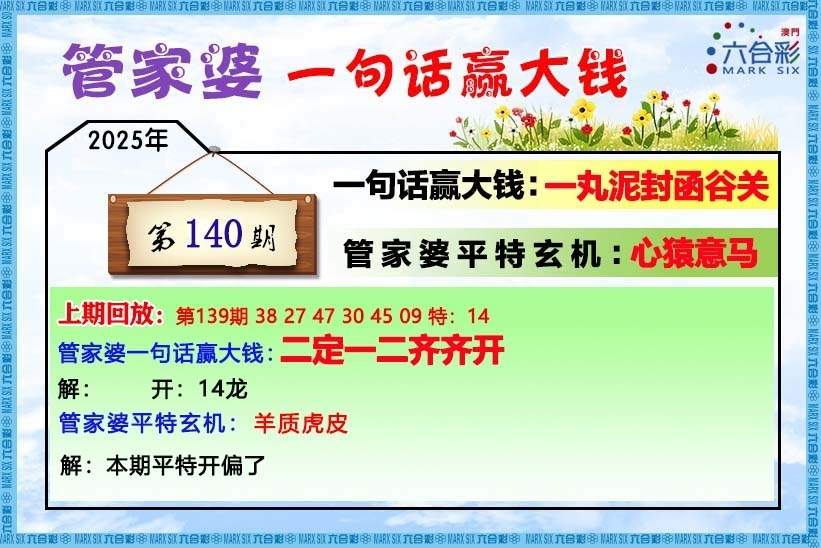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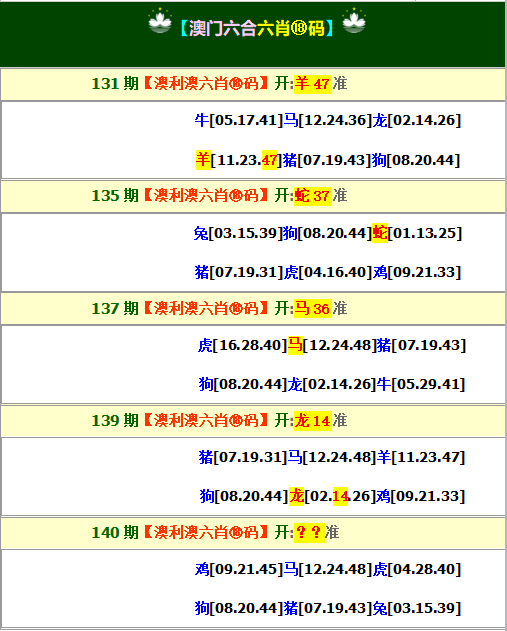

140期小小分析:【十二生肖版·冤蛛记】鼠(机警)如蛛察异样,轻触鸡(暴躁)惹祸端;虎(威猛)未辨先咆哮,兔(谨慎)缩角冷旁观;马(耿直)冲锋啄凶手,蛇(阴冷)暗笑局外盘;狗(忠诚)复盘真相后,蛛冤终得羊(温良)叹。生肖喻世相:鸡莽、虎躁、兔怯、马愣、蛇猾、狗义、羊慈——警醒世人莫让偏见遮蔽双眼,冲动易酿冤案
综合特肖:鸡虎兔马蛇狗羊
主攻四肖:鸡虎兔马
主攻特码:09.21.16.28.15.27.36.37.08.35
139期小小分析:【十二生肖版解读】兔(主角受伤,柔弱却坚韧)狼(未直接出场,但对应狗生肖,戌狗近狼性,象征危机)鸡(鸭子以酉鸡代,羽族同类,守护啼晓之意)马(腿伤暗合午马奔蹄受损,呼应康复期)羊(未羊温厚,象征鸭子安抚的温柔)龙(辰龙代表痊愈希望,如龙腾云重生)猪(亥猪福运,隐喻结局转机)寓意:危局中(狗/狼)得盟友(鸡/鸭),伤患(马/兔)终迎祥瑞(龙/猪),羊性温柔护佑全程。(注:7生肖含兔、狗、鸡、马、羊、龙、猪)
综合特肖:兔狗鸡马羊龙猪
主攻四肖:兔狗鸡马
主攻特码:15.27.08.20.09.21.36.35.14.31
138期小小分析:故事讲述母爱的纯粹与身份认知的困惑——鸡妈妈用温暖孵化异类,跨越血缘守护生命,最终在差异中领悟爱的真谛。【生肖演绎】鸡怀揣疑惑仍紧抱怪胎;狗幼崽懵懂吮吸养恩;牛默默见证这场错位亲情;兔啃着胡萝卜感叹世事难料;马嘶鸣着提醒主人荒唐;羊跪乳反哺诠释无私之爱;猪呼噜着说:长得不像也是娃。(保留核心角色鸡狗,加入牛马羊猪兔作为旁观者,既维持故事主线,又通过动物特性丰富寓言层次,暗喻超越血缘的母爱伟大。)
综合特肖:鸡狗牛兔马羊猪
主攻四肖:鸡狗牛兔
主攻特码:09.21.08.20.05.17.15.24.35.19
137期小小分析:主人召开接球大会,虎教练叼着名单踱步,兔秘书速记时撞翻胡萝卜。龙裁判喷火计分牌吓跑蛇选手,马选手扬蹄抗议:我叼球跑最快! 猴捣蛋鬼偷藏奖品香蕉,狗保安小黄急得狂吠:汪!球被我埋后院了! 突然鼠小弟举奖杯钻出:嘿嘿,趁乱捡漏我第一!(虎/兔/龙/蛇/马/猴/狗七生肖乱入,暗讽职场闹剧)彩蛋:真正赢家或是缺席的猪——躺着睡觉没参会,反逃过一场混战
综合特肖:虎兔龙蛇马猴狗
主攻四肖:虎兔龙蛇
主攻特码:16.28.15.27.14.26.37.36.34.08
136期小小分析:这段文字讲述弱小兔子如何用智慧赢得公鸡保护的寓言,用7生肖诠释其深层智慧:兔(主角,示弱藏智)鸡(保护者,彰显仁义)鼠(暗中观察,学习兔子的生存策略)羊(温顺配合,如同兔子的柔弱姿态)猴(象征兔子最终使用的巧妙方法)狗(忠诚守护,呼应公鸡的保护本能)猪(憨厚包容,暗喻结局的圆满)寓意:弱者以柔克刚(兔),智者借力而行(猴),仁者自然获助(鸡)。兔子可能假装受伤或帮公鸡觅食,用互利思维激发保护欲
综合特肖:兔鸡鼠羊猴狗猪
主攻四肖:兔鸡鼠羊
主攻特码:27.39.09.21.06.18.35.34.08.19
- 澳门四不像
- 澳门传真图
- 澳门跑马图
- 新挂牌彩图
- 另版跑狗图
- 老版跑狗图
- 澳门玄机图
- 玄机妙语图
- 六麒麟透码
- 平特一肖图
- 一字解特码
- 新特码诗句
- 四不像玄机
- 小黄人幽默
- 新生活幽默
- 30码中特图
- 澳门抓码王
- 澳门天线宝
- 澳门一样发
- 曾道人暗语
- 鱼跃龙门报
- 无敌猪哥报
- 特码快递报
- 一句真言图
- 新图库禁肖
- 三怪禁肖图
- 正版通天报
- 三八婆密报
- 博彩平特报
- 七肖中特报
- 神童透码报
- 内幕特肖B
- 内幕特肖A
- 内部传真报
- 澳门牛头报
- 千手观音图
- 梦儿数码报
- 六合家宝B
- 合家中宝A
- 六合简报图
- 六合英雄报
- 澳话中有意
- 彩霸王六肖
- 马会火烧图
- 狼女侠客图
- 凤姐30码图
- 劲爆龙虎榜
- 管家婆密传
- 澳门大陆仔
- 传真八点料
- 波肖尾门报
- 红姐内幕图
- 白小姐会员
- 白小姐密报
- 澳门大陆报
- 波肖一波中
- 庄家吃码图
- 发财波局报
- 36码中特图
- 澳门男人味
- 澳门蛇蛋图
- 白小姐救世
- 周公玄机报
- 值日生肖图
- 凤凰卜封图
- 腾算策略报
- 看图抓码图
- 神奇八卦图
- 新趣味幽默
- 澳门老人报
- 澳门女财神
- 澳门青龙报
- 财神玄机报
- 内幕传真图
- 每日闲情图
- 澳门女人味
- 澳门签牌图
- 澳六合头条
- 澳门码头诗
- 澳门两肖特
- 澳门猛虎报
- 金钱豹功夫
- 看图解特码
- 今日闲情1
- 开心果先锋
- 今日闲情2
- 济公有真言
- 四组三连肖
- 金多宝传真
- 皇道吉日图
- 澳幽默猜测
- 澳门红虎图
- 澳门七星图
- 功夫早茶图
- 鬼谷子爆肖
- 观音彩码报
- 澳门不夜城
- 挂牌平特报
- 新管家婆图
- 凤凰天机图
- 赌王心水图
- 佛祖禁肖图
- 财神报料图
- 二尾四码图
- 东成西就图
- 12码中特图
- 单双中特图
- 八仙指路图
- 八仙过海图
- 正版射牌图
- 澳门孩童报
- 通天报解码
- 澳门熊出没
- 铁板神算图
- 杀料专区
- 独家资料
- 独家九肖
- 高手九肖
- 澳门六肖
- 澳门三肖
- 云楚官人
- 富奇秦准
- 竹影梅花
- 西门庆料
- 皇帝猛料
- 旺角传真
- 福星金牌
- 官方独家
- 贵宾准料
- 旺角好料
- 发财精料
- 创富好料
- 水果高手
- 澳门中彩
- 澳门来料
- 王中王料
- 六合财神
- 六合皇料
- 葡京赌侠
- 大刀皇料
- 四柱预测
- 东方心经
- 特码玄机
- 小龙人料
- 水果奶奶
- 澳门高手
- 心水资料
- 宝宝高手
- 18点来料
- 澳门好彩
- 刘伯温料
- 官方供料
- 天下精英
- 金明世家
- 澳门官方
- 彩券公司
- 凤凰马经
- 各坛精料
- 特区天顺
- 博发世家
- 高手杀料
- 蓝月亮料
- 十虎权威
- 彩坛至尊
- 传真內幕
- 任我发料
- 澳门赌圣
- 镇坛之宝
- 精料赌圣
- 彩票心水
- 曾氏集团
- 白姐信息
- 曾女士料
- 满堂红网
- 彩票赢家
- 澳门原创
- 黃大仙料
- 原创猛料
- 各坛高手
- 高手猛料
- 外站精料
- 平肖平码
- 澳门彩票
- 马会绝杀
- 金多宝网
- 鬼谷子网
- 管家婆网
- 曾道原创
- 白姐最准
- 赛马会料